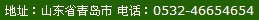|
词 裴聪敏/诵 谭红平/图 网络 垣曲味道 垣曲这个地方有意思。中条山从西南上溯东北款款上来,围了大半圈;太行山从东北直直下来,到王屋山戛然而止,愚公移山把土倒成了那么多的丘陵;黄河从山西的西边直泻南走,大概眷恋这个地方,在风陵渡拐了个弯,过芮城、平陆光顾垣曲,在县域的南边划半个圈。山绕水围,如垣似曲,名符其实。 有山有水,有原有川,地处晋豫之交,东走是中州平原,西去乃晋南盆地,北边翻过山是晋东南的潞府泽州,南边过了河是渑池新安,属河南省境域。周边与两省六市八县接壤,左邻右舍、嫡亲远朋。各种风情民俗在这里相映交辉,形成独特的文化。语言不同,风俗有别,就连吃食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。这里说几种吃食,纸上谈兵,在字里行间品尝垣曲的味道。 锅盔 天刚亮,宝玉就起床了。洗把脸,就开始了一天的活路。 宝玉的店面在三八路的半坡上,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,靠墙角垒了个灶台,紧挨着灶台放着一匹案板,剩下的地方站三个人就转不开身了。反正他做的生意不煮面,不炒菜,不摆桌搁椅,顾客买了拿回去吃,这地方就够了。 掀开瓷盔,面发的满满荡荡,老酵的化学反应和物理作用在表皮上撑开一道道裂纹,横七竖八地迸发着能量。抓开表皮,成丝成咎,揪起一团,香味扑鼻。 把面从盔里挖出来,摊在案板上,使醎,掺面,一遍一遍地揉,反反复复地搓,硕大的面团在粗壮的手掌中波澜起伏。揉面是力气活,一阵功夫,宝玉额头上沁出了汗珠,肩头有些酸。门外,晨练的人们踢踢沓沓走过,屋里,宝玉的晨练是这案板上的运动。 宝玉是打锅盔的。锅盔是垣曲的地方吃食,一种直径尺余、一指多厚的圆形大饼。垣曲人大饼叫旋,小饼子叫坨坨,锅盔和旋差不多,都是面做的,形状差不多,旋是烙(垣曲人读bo)出来的,锅盔是打出来的,做法不一样,吃着味道不一样,名字当然不一样, 别的地方也有锅盔。垣曲的锅盔是咋来的?宝玉小时候听爷爷说过。当年李自成进京,从陕西一路厮杀过来,到了垣曲驻营扎寨,休整补充,陕西人当然做秦地饭食。西北重面食,喜面条,善烙饼,宽面窄粸,大旋小饼地吃,陕西有种大饼,半拃厚,硬的用刀削着吃,耐饥,容易保存,即是吃食,又当干粮。于是李自成下令做这种饼。垣曲的物产、吃食和陕西差不多,面好吃、面筋道,就在石板上烙大饼。战事紧,需求量大,灶下烧火反来复去地烙的慢,有人灵机一动,把头上戴的铁盔取下来,把灶里烧的炭火放进头盔,扣在鏊上面烤。熟了,一尝,又香又酥,味道不错。就这样,一种吃食在农民起义的征途中产生了,在兵刃厮杀中诞生了。因为做这种饼即用鏊又用战盔,就叫锅盔,从某种意义上说,锅盔是军民合作的产物,秦晋之好成就了一道美食。 李自成走了,留下了故事,留下了遗迹,也留下了锅盔。过了多少年多少代,西北风情和中原的味道在垣曲揉到了一起。打锅盔仍然是灶下烧火,灶口放鏊,鏊上盖块铁板,用泥糊成盔形,里面也烧火。垣曲有木炭,木炭好,后来就把柴变成了木炭,上面烙下边烤,没有烟熏火燎,做锅盔仍然叫打锅盔,有硝烟战火的味道。 锅盔的来历只是听爷爷这样说过,他们家三代打锅盔是有历史的。宝玉姓丁,祖籍东原,当年爷爷来到垣曲城,进饭铺学徒,学的是面案。那时垣曲城里的饭铺卖的只有羊汤、锅盔、饸饹、汤面几种吃食,爷爷就擀粸(面条)、压饸饹、打锅盔,和面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后来父亲理所当然地上了面案,站在爷爷的肩膀上探日月,面案功夫风生水起。面条滑溜。饹饸细长,锅盔焦黄,在城里有了名气。尤其是锅盔,十里八乡,七州八县,谁不知道! 到宝玉能上面案的年龄,正赶上改革开放,市场繁荣,城关成了古城,饭铺成了食堂,不长的街道上食堂一家挨着一家。传统的吃食和现代的风味交相辉映,饸饹锅盔与蒸炒煎炸并驾齐驭。宝玉跟着父亲打锅盔、压饸饹,也许有祖传基因,也许从小在锅盔饸饹里长大,没多久,宝玉的手艺就独当一面,有声有色了。 不可否认,在物欲横流的时代,南甜北咸,东辣西酸,川菜鲁味,生猛海鲜,纷至沓来。各式各样的饼子诱惑着垣曲人的味蕾,烧饼、酥饼、菜盒、芝麻饼,荆州的戈块,新疆的馕,就连武大郎的炊饼也晃晃悠悠地从山东来了。烤的、烙的、煎的、油炸的、电饼铛做的。人们的味觉感官与时俱进。垣曲的锅盔依然是炭烙炭烤,泥糊的锅盔鏊古老笨重,喧闹的尘嚣掩盖了锅盔的味道。门前冷落车马稀。宝玉的门面从一间到半间,生意从街上做到家里。 古城淹了,古城搬迁了,古城锅盔的味道没有被淹没,锅盔鏊和宝玉搬到了新地方。安装在新居的东屋里,雪白的墙壁,锃亮的瓷砖,吊在墙角的锅盔鏊显的有些深沉。 宝玉有时也打锅盔,味道在村舍小巷里时有时无地飘荡,渐渐地被人遗忘了。偶而有人提及,也只能是咂咂嘴,从记忆深处寻找那曾经的味道。 盐多不是饭,大鱼大肉也有吃腻的时候。慢慢地,人们的饮食观念转移到对饮食文化的渴求。米粸上了宴席,起糕招待宾客,捞饭,焖饭成了稀罕吃食。地道的锅盔饸饹理所当然地成了垣曲饮食的金字招牌。就有人烙旋,厚厚的起面旋说是锅盔。指鹿为马,鱼目混珠,好在都是面做的,双兔傍地走,安能辨我是雄雌? 其实锅盔和旋是一对表兄弟,制作工艺的不同,口感味道当然不一样。旋是烙熟的,锅盔是又烙又烤打出来的;旋吃到嘴里软绵,锅盔入口酥香;旋泡进羊汤中就化了,锅盔泡进羊汤不烂不散,有味道,有嚼劲;锅盔十天半月不坏,旋搁三天就有了斑点。 宝玉把锅盔鏊拾掇拾掇,久违的味道又回来了。路边贴了招牌,算是做广告。不时有人慕名前来寻味;乡镇招待客人也用锅盔,甚至送礼也掂几个锅盔,毕竟是一方水土的名吃,经济实惠;儿孙满月、上梁搬家,也把锅盔作礼馍,厚重朴实的风采,金黄亮丽的色调,彰是喜庆韵味,星星点点的芝麻,寓意节节高,古老的锅盔赋于了新的内涵。有人从锅盔看到商机,把宝玉的锅盔发到了网上,推进了淘宝,快递到全国各地;有一司机路过古城,闻香寻迹,拜师学艺,锅盔打到了河南;省里、市里的电视台采访录像,垣曲锅盔上了电视,宝玉当然露了脸。 宝玉还是一如既往地打锅盔,只是在县城租了门面,从古城打到了新城。 生火,引燃木炭。炭火在鏊盔中劈劈啪啪地爆燃,火苗从顶上的圆孔里窜出来,点点火星从抬鏊的砖头缝隙溅出来。刚生着的木炭火劲爆,鏊热的不匀,先打两锅烧饼。让火劲冒冒,就象运动员比赛前热身一样。 差不多了,从面坨上切下一块,称量、揉面,不抹油,不添物,用传统手法激发面香色味。擀扙擀圆,手掌研饼,掌心在面皮上动,面随掌心转,厚薄一样,是掌上功夫。锅盔饼做好,用刀尖在边缘划一圈,在面饼上撇拉几道,看似随意,其有奥妙。 一手抓住压杆,一手扶住鏊绊,压起上鏊,起鏊、擦鏊,托饼,进鏊、刷水、撒芝麻、盖鏊。手法娴熟,程序严谨,有条不紊。 这套锅盔鏊,还是爷爷当年使唤过的,交给父亲,又传到了宝玉手里。一盘鏊,三代人,不知道打了多少锅盔,岁月一层层留在生铁铸的鏊上,黑的锃亮;铁打的吊环磨偏了芯;木头压杆手抓手磨成了细腰。宝玉打锅盔还是用的这套锅盔鏊。 木炭在鏊盔中静静地燃烧,炙热的能量从盔底传进鏊里,灶下的炭火悄悄地推波助澜。下面有火,上面有火,锅盔在鏊里承受上烤下烙,两面夹击。打锅盔,没有蒸煮的喧闹,也不象煎炒那样的热烈。不冒热气,没有烟雾,不听瓢响勺碰,不见止剑动戈。只是盔鏊封闭,无法察颜观色,生熟、火色,靠感觉,凭经验。说打锅盔,实实地委屈了这个打字。 在锅盔家族里,还有一种叫锅盔牙的,比锅盔更酥,更香,当然配料也不一样,制作工序更繁杂,也更好吃。不过现在没有几个人能打的成。就是锅盔,也有一定的技术,做酵,和面,面和的软硬,碱使的多少,甚至天气的阴晴,四季的变化,和面水的温也有差异。烧什么木炭,火力的强弱都可能影响锅盔的火色、口感。打锅盔有技术也有秘诀,有实践也有悟性,全凭功夫,凭心领神会。要不,旋人人会烙,而锅盔只能是饭铺卖的吃食。想当年,能吃一份锅盔是莫大的享受,装在口袋里,掐一小块吃进嘴里,细嚼慢咽,唇齿留香,三天舍不得漱口刷牙。 火候到了,吊盔鏊,转锅盔,垫铁片、补色。又一番拨弄,再搭上盔鏊。少倾,锅盔熟了,起鏊、刷水,提色,出锅。 这就是锅盔,垣曲的锅盔。墩厚朴实,外刚里柔,面味火色跃然其上。略厚的边缘微微翘起,气宇昂然但不失纯朴厚道。底部火色浅浅,一簇一簇的叫核桃花。表面上,窄窄的一圈乳白方显本色,鲜鲜亮亮的一片金黄留驻了火颜,条条裂纹,点点芝麻,似大地纵横,如春华秋实。散发出特有的味道。弥漫街市,香诱路人,闻香停车,知味进店…… 宝玉依然打锅盔,依然恪守着传统,一丝不苟地打锅盔,用锅盔鏊传承锅盔文化,守护垣曲的味道。 作者简介 裴聪敏,山西垣曲人,电影工作者。中国电影放映协会会员,垣曲县作家协会常务理事,垣曲县舜文化研究会理事。曾在《电影故事》《新电影》《电影普及》《舜乡》《舜文化研究》等刊物发表文章。对垣曲人文、民俗、农耕文化研究较深。 读者简介 谭红平,垣曲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,主任记者,垣曲县朗诵艺术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。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13801256026.com/pgjg/pgjg/1757.html |
当前位置: 垣曲县 >朗读亭垣曲味道之锅盔
时间:2022/9/26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分叉路口的幸运女孩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